2022年5月29日,上海师范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所长、哲学与法政学院光启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作翔教授应法学院邀请,作了题为“关于建立分种类、多层级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的思考”的学术讲演。本次讲座在腾讯会议和哔哩哔哩平台同步直播。讲座由法学院副院长柳建龙副教授担任主持人,王莉君教授、田夫副研究员以及黄钰洲讲师担任与谈人。

在讲座中,刘作翔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动因。他指出,从理论上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的命题,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也对于社会规范的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从实践来看,社会规范的备案审查制度目前仍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研究和实践领域。而且近年来,由于缺少对于社会规范的制定和发布的有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社会规范存在着违法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
接着,他对社会规范的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并根据其表现形式,分为五大种类,分别是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社会组织自制规范,以及各级政治权威机关制定的专门用于管理内部成员的自制规章。
建立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在于:它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面对社会规范引发过多问题所应当采取的解决方式。刘作翔教授以“上海迪士尼乐园禁带食品入园搜包案”等典型案例,说明现实生活中村规民约、大学自制规章和企业规章等社会规范普遍存在问题并频频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甚至造成违法现象。
对于如何建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刘作翔老师提出,我国现实中存在的网格化的社会网络结构,可以将各种社会组织自制规范的制定主体纳入其中,并形成隶属关系,由此可将社会规范层层分解,交由其主管机关、登记机关、监督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要求落实到位,这为建立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以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公司律师制度、社会律师制度为载体的现代社会发达的法律服务体系,以及其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也可以发挥社会规范备案审查的主力军作用。
而后,他指出,对社会规范进行备案审查需要遵循合宪性,合法性、合理性、合规性、适时性以及可适用性、可操作性、可实践性等标准,并且采取内部审查与外部审查相结合的办法,各担其任、各负其责,将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最后,他总结道,讲座主题中所说的“分种类”指的就是根据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划分的五大种类;“多层级”指的是除了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社会自生规范外,其他社会规范均有其组织体系和层级体系。将社会规范层层分解后,审查主体根据法律法规履行各自职责,以此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对社会规范备案审查的体系化、系统化的制度框架,使各种社会规范类型步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提高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目标。
随后,主持人与三位与谈人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刘作翔教授对此一一回应。其中,柳建龙副教授认为在备案审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数量庞大的社会规范会挤占行政资源。王莉君教授担忧,主管机关并非由纯粹的法律职业者构成的主体,可能不具备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能力;而对社会规范进行严密的备案审查,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空间扩大,破坏了社会规范的活力。田夫副研究员认为对社会规范进行备案审查可能过于强调了法治的积极面向,而干预了公民的自由。黄钰洲讲师则从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对家长制风格的审查、监督、控制可能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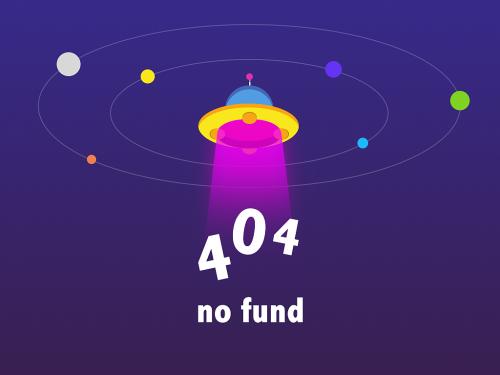
刘作翔教授首先强调,建立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和公民的利益。他回应道,如果备案审查成为行政机关的一项职能,行政机关便有义务完成。目前应论证对社会规范进行备案审查的必要性,而非审查主体的能力问题。目前这个问题仍处于学术讨论阶段,有些问题诸如对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社会规范的备案和审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至于对备案审查扩大行政权力以及影响社会自治的担忧,刘作翔教授表示,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当务之急是寻找社会规范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强调我们还是应该关注实践,立足于具体的实践问题,意识到社会规范侵害公民权利的案例普遍存在并带来的社会危害。
关于对于社会规范存在问题的救济机制,王莉君教授与田夫副研究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田夫副研究员认为,是否存在其他的手段替代备案审查制度来发挥作用;王莉君教授则详细地提出是否可以通过利用集体诉讼的方式,使违法的社会规范得到纠正。
刘作翔教授强调,司法虽是解决社会规范存在问题的有效手段,但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手段,有局限性,对于有些损害是无法恢复的;且司法只解决个案问题,无法救济到每一位受到侵害的公民,且消耗的资源远远超过事先审查消耗的资源。至于是否存在更好的办法来替代备案审查制度,他希望集思广益、共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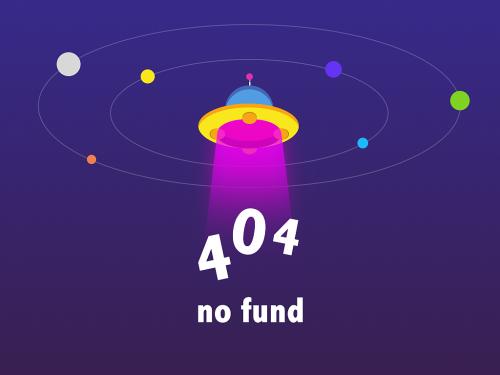
此外,王莉君教授认为,规范性文件的界定仍需进行探讨。目前对于行政立法性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的区分存在困境,程序标准易导致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之名行立法之实,对公民的权利义务造成影响;而实质标准无法真正区分“创设权利义务”和“权利义务的具体化”的差异。她还认为,高级人民法院颁发的司法指导性文件得到了地方法院的高度重视并予以执行,但它似乎并不在“专门用于管理内部成员的自制规章”的范围之中,因此,刘作翔教授的限定或许略显狭窄。
对此,刘作翔教授表示,在实践中,规范性法律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的定义是模糊的,应当首先厘清两者的概念。对于王莉君教授提出的行政立法性文件和规范性文件的区分存在判断上的困境,刘教授认为,应以形式判断为主要判断标准,实质判断无标准可循,易导致混乱。他认为,王莉君教授对规范性文件的概念存在误读,他对狭义规范性文件的界定包括各级审判机关发布的司法规范性文件,因此高级人民法院颁发的司法指导性文件应在狭义规范性文件的范围之内,而他提出的“专门用于管理内部成员的自制规章”是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
田夫副研究员对于社会规范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将规范分为社会规范和技术规范,受到了苏联将规范分为伦理规范和技术规范的影响。而从伦理规范到社会规范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传统的重构。
刘作翔教授则赞同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相对应的观点,且社会规范具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其概念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他并不赞同国家和社会的二分,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方法对学者影响较大。
田夫副研究员提出疑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的“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的命题,是否可以分为“国家生活法治化”以及“社会生活法治化”?此时,两个“法治化”的意义是否一致?此外,他认为,刘作翔教授提及的网格化理论的充分性仍需探讨。
刘作翔教授回应道,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是有区别的,两个“法治化”的涵义自然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需要对什么是国家生活,什么是社会生活进行界定和论证。他强调,网格化并非一个理论,而是建立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的事实前提和基础。
而对于田夫副研究员提出的“应该根据社会规范的性质及其主体的性质,来区分审查的强度和标准”的观点,刘作翔教授表示高度认同。
最后,针对网络平台端提问中关于“对内的规范是否不需要审查”的疑问,刘作翔教授认为,对内规范也切实影响到了许多人的利益,需要对其进行审查;但哪些事项需要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至此,一场内容丰富、精彩绝伦的讲座完满结束。
撰稿 | 蒋 涵(法学院21级本科生)
校稿 | 张静怡(法学院20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