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晚清日本法政大学为清国留学生举办的法政速成科是近现代中日交流历史中的重要一环。其所组织刊行的《东洋》杂志,与著名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皆采用独特的汉文形式出版,但长期以来缺乏讨论。1906年8月该杂志先由法政大学校友发起,后改由校方主办,曾经受到当时政界、学界人士广泛关注。在主笔久保天随主持下,不仅收载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历史、宗教等领域专业学术论文,更对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清朝内政外交多所讨论,具见当时主事者试图以智识启发影响中国、进而统治经营“东洋”诸国之用心。其所蕴含之思想特征较为复杂,且表现出诸多层次,对于今日了解二十世纪初年日本知识精英对于晚清政治改革的历史见解很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政速成科;东洋;中日关系;留学教育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4期。
在近现代百余年中日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交流历史进程中,日本法政大学一度为清国留学生开设的法政速成科(1904-1907)以其突出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影响,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该议题的重量级别似乎并不匹配。相关历史资料的探索、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开展。本文所欲揭示的这份《东洋》杂志,便是有关法政速成科的林林总总亟待开发的史料资源中的一例。
1988年日本法政大学出版《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在该书第四部分(广告)和书末安冈昭男(1927-2016)教授撰写的《解题·清国人留日学生与法政速成科》一文中,对《东洋》杂志有过简单介绍,并揭载了该杂志创刊号的目录。截至目前,用中文在中国大陆发表的关于法政速成科的著作或论文中,尚未有人对该杂志进行过全面介绍或者评价。最近数年,仅在王敏发表的《站在巨人的肩上的记述——日本法政大学与辛亥志士》和《关于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与辛亥志士的考察》两文中,见其用较为简略的文字从侧面提到过该杂志。或许因为该杂志不易获见,以致国内研究者很少注意及之。谨撰此文,拟就《东洋》杂志的出版发行、内容构成、思想特征等情况略作引介。
壹、《东洋》杂志的出版发行
据日本法政大学安冈昭男教授介绍,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法政大学除日文刊物《法学志林》外,曾经针对新创办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汉文形式印刷发行过两种特别的出版物:其一为著名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于1905年2月5日开始发行;其二即为《东洋》杂志,创刊于1906年8月15日。众所周知,大致与此同时,在清末赴日留学热潮下,曾有不少留日学生组织社团汲汲引进新学,或将日文书籍译成汉文(如大型政法类丛书《法政丛编》、《法政萃编》),或在日本用汉文出版刊物(如《法政学交通社杂志》、《法政学报》)。他们不仅将这些出版物在日本——尤其是留日学生之间广泛传播,更将之转贩回国,意图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学术之走向。但鉴于法政速成科的突出影响,故而在彼时日本出版发行的为数众多的汉文出版物中,《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和《东洋》杂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该讲义录和杂志是专门为当时的留日法政速成学生创办发行的,因而内容方面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第二,该讲义录和杂志皆由日本法政大学校方或由与校方具有密切关系的日方人物主持,而不是出自留日学生之手;
第三,该讲义录和杂志虽然也用汉文刊行,但基于上述两点,这种由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创办,却特别采用汉文形式刊行,别具一格。揆其原因,无外乎主事者考虑到当时清国留日学生的日文和专业水平有限,为求读者阅读便利,提高知识传播效率,而刻意采用如此变通手段。
《东洋》杂志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8月15日正式创刊发行。在创刊号的卷首位置,特别载有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贺辞,以及大隈重信(伯爵)、杨枢(驻日公使)、梅谦次郎(法政大学总理)、范源廉(学部参议官)、王克敏(驻日公使参赞官)、夏同龢(广东法律学堂总监)等人的祝辞,颇极一时之盛。该杂志原拟每月15日出版,属于月刊性质,但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至次年9月28日发行第十号后,即被迫终刊,前后发行仅10期(号)而已。
经查该杂志第一号卷末凯发登录入口的版权页上所标注出版信息,发行兼编辑者为关安之助,印刷者为关善作,印刷所为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发行所则署名为东洋社。并且,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大陆设有4家代售公司:在日本的两家均位于东京的神田区,一为东京堂,一为上田屋;在中国大陆者,一为上海的广智书局,一为汉口的昌明公司。然而,此仅为最初情形,后来颇有变化。我们在该杂志第二号卷首发现一则署名“法政大学”的启事,其中透露了一些重要线索,谨录于下:
“本志为本大学校友有志者所组织之东洋社创刊。原以研究清国之政教各方面事情,以供其参考为目的。惟是清国内地之事情及其一般教育之程度,若不精通透悉,恐其目的未可遽达。于是同社利用本大学总理梅博士清国漫游之机会,派社员同行,周游各地,精密调查。现已归来,将继续发刊矣。而本大学亦抱有同一趣旨之希望,因与同社协商,将同社之事业全部移归本大学接办。以后本志即由大学发刊。”
由上可见,该刊先是由法政大学校友所组织的“东洋社”创办,自始即与法政大学有着密切关联,甚至在该校总理(校长)梅谦次郎1906年漫游中国之际,更派社员随同前往,“周游各地,精密调查”。及至考察归来,校方考虑到该社创办宗旨与该校“趣旨同一”,经过协商,乃将杂志“全部移归”大学接办。该杂志被接办后,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均有所变动。自第二号起,发行兼编辑者改为萩原敬之,印刷者改为重利俊夫,印刷所改为金子活版所,发行所则改为“私立法政大学”。及至后来,我们在第七号凯发登录入口的版权页上更是发现,该杂志的代理销售公司也由原来的4家增至7家,分别为:位于日本东京神田区的三省堂、东京堂、有斐阁、奎文馆,位于中国上海的广智书局,上海和汉口的昌明公司,以及天津的东亚公司支局,发行渠道显著增加。
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该杂志第二号的实际发行日期为明治四十年(1907)1月28日,距离创刊号的发行日期(1906年8月15日)已过5月有余。原定每月15日刊行的月刊杂志,何以刚刚创刊,便会发生如此耽搁?依笔者之见,或与1906年梅谦次郎的中国之行有直接关系。上引“启事”云:“同社利用本大学总理梅博士清国漫游之机会,派社员同行,周游各地,精密调查。现已归来,将继续发刊矣。”从其行文逻辑看,似可认为:由于《东洋》杂志派社员随同梅谦次郎考察,所以耽搁了发刊。该社派往中国随同梅谦次郎考察的“社员”,在《东洋》杂志的编辑发行过程中,起着重要甚至核心作用。
另外,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载有一则短讯,使我们对这名东洋社社员的情况多了一点了解。其中谈道:“本社员永原寿太郎氏,将与梅法学博士俱漫游清国,视察其风土人情,发程在近日。于是知友相谋,张祖筵于红叶馆。来会者百余名,颇极盛宴云。愿一路平安而归来,所赍奚囊之富,吾人之所不堪切望也。”由此可以明确,当年随同梅谦次郎来中国访问的东洋社社员,即为永原寿太郎。遗憾的是,对于永原寿太郎的其他情况(如生卒年月、教育背景、任职履历等),我们从汉文和日文材料中所获信息实在少得可怜,仅在若干中国媒体(如《申报》)和几位著名人物(如严修、丘逢甲)的日记、诗词中,发现永原曾经随同梅谦次郎漫游中国的零星记录。另在《东洋》杂志第三号的卷首,载有永原寿太郎随同梅谦次郎访问南京时与当地的法政大学校友合影一张,属于难得的历史影像记录。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法政大学的“东洋社”作为《东洋》杂志的重要发起者,究竟由哪些人组成,我们所知亦属有限。除了永原寿太郎之外,我们通过伊藤博文的祝词,得知光村利藻是该杂志创刊时的重要参与者;以及在创刊号的一篇时论文章的末尾,发现一位社友的笔名(也可能是字号)——“蠖堂”。此外,我们现在对于东洋社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但是,永原寿太郎作为《东洋》杂志的重要成员,应无疑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永原寿太郎是《东洋》杂志社的重要一员,并曾陪同梅谦次郎访华,却非该杂志的主笔。安冈昭男教授曾经指出,该杂志以“汉文学者久保天随任主笔”。今从该杂志创刊号所刊载的文章来看,作者比较分散,“主笔”的色彩并不明显。但自第二号起,每期“主张”或“社说”栏目主旨论文基本都出自日本法政大学的另一位教员——久保天随之手,基本可以验证前述说法。
久保天随,本名得二,以天随为号,又号默龙、青琴、兜城山人、兜城生、虚白轩、秋碧吟庐主人等。1875年7月,出生于日本东京。189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转而进入该校大学院就读。1902-1906年,担任法政大学讲师。1920年,出任宫内省图书寮编修官。1927年11月,以元曲研究获颁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4月,受聘为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东洋文学讲座教授。1934年6月,因病在台北住所逝世,享年60岁。久保天随一生著述宏富,早期著作《日本儒学史》(博文馆,1904)、《近世儒学史》(博文馆,1907)、《支那文学史》(平民书房,1907)等,颇具开创性。
中晚期之元曲研究,亦在日本开风气之先。在汉诗方面著有声名,在台期间,曾筹组“南雅诗社”,多所唱和,刊有《秋碧吟庐诗钞》五帙十四卷。久保天随去世后,平生所藏图书由台北帝国大学购入,现为台湾大学珍藏。
自《东洋》杂志第二号起,久保天随发表署名文章《上古印度之文化及其东渐》,其后每号均刊有他的署名作品,内容涉及日本外交史、中国政治、宗教思想等多方面,包括他以《秋碧楼诗剩》的名义刊载的诗词作品。并且,经常是多篇文章同时刊载于一期刊物之中,甚至在第四号和第七号的附录中,还曾连载其撰写的《朝鲜现代史》。种种迹象表明,久保天随作为《东洋》杂志主笔角色是当之无愧的。
贰、主要内容构成
正常情况下,一个刊物的内容构成及编排形式,往往由它的办刊宗旨所决定;换言之,刊物内容及编排形式应该服务于它的办刊宗旨,故在介绍《东洋》的内容构成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刊登在《东洋》杂志创刊号上的《发刊辞》,是我们了解其办刊宗旨的最佳材料。
该《发刊辞》首先从疆域、人民、物产三个方面,揭纛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五洲广矣,种族众矣,而疆域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夥,莫若我亚细亚洲。”进而提出,亚洲之中“建国最久最著”的四个国家——中国(支那)、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安南)——自古以来,“玉帛通好,唇齿相依”,曾经创造了“独立于东洋,雄视于宇内”的辉煌历史。但自中世以降,时势逆转,欧美各国蒸蒸日上,国富兵强,不断扩张版图,攫取利权,以致安南(越南)被法国吞并,朝鲜“仅得自立”(实为日本侵占),中国因为物产丰饶、土地肥沃,也“久为列强所垂涎”。接着,结合当时国际形势指出,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方面“大有所警,君臣宵旰,致力内治”,清朝政府则“锐意以改革宿弊,收回利权为事”,韩国(朝鲜)也准备“厘革诸政”。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因循姑息,坐观其变”,而不积极进取,“徒恃往时文物之盛”,“东洋三国”——中国、日本和朝鲜——则势必沦入亡国灭种的境地。所以,该杂志呼吁:“东洋三国”应该“协心戮力,研钻学术,启发知能,内敦其交,外御其侮”,力图恢复“往昔国运之隆,文物之盛”。
为达此一宗旨,在《东洋》杂志的主事者看来,“凡百政治、法律、经济,以至文学、技艺,苟有可以为启发智识,挽回国运之助者”,皆应“洪纤并举,网罗综括,以为交换智识之机关,善邻辑睦之键钥”,以图对于“国步之进运发展”有所裨益。这其中不无站在世界格局的高度,从东亚地区利益考虑之意。但进一步言之,该杂志选择汉文形式出版,以清国留日学生为特定直接发行对象,究其实质,乃是着眼于研究中国清朝的内政外交,希图以刊行杂志的方式,通过影响留日学生——乃至中国国内的知识界,进而影响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之趋向。
该杂志上述创刊宗旨,在当时赢得广泛共鸣。即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题词中说,“苟任其责,则操觚从事编辑者,明目张胆,宜注意于政治、文学,而国际外交之否泰,贸易通商之盛衰,工艺进步,风俗改善,凡醒觉人之耳目者,爬罗剔抉,务期靡遗”。大隈重信则在祝辞中言道,当他看到“有志之士相谋发刊新志《东洋》,欲以敦善邻之谊,供开发智慧之资”,认为此举很是伟大,并且很切合时宜。不仅如此,清朝的醇亲王载沣在给《东洋》杂志的题词中,更是龂龂以“志兴东亚”相期许。时任法政大学校长(总理)的梅谦次郎,也十分认同此宗旨,认为在增进知识的诸般手段中,定期刊行杂志,是一种较为便捷的方法。所以,《东洋》杂志发刊之际,即便他身在朝鲜,也特地发信表示祝贺,用他自己的话说,实“满腔之赞成而不能禁也”。
基于前述宗旨,《东洋》杂志在内容上主要侧重三个方面:(1)介绍晚近西方政治、法律、经济等社科专业知识;(2)研究中国清朝内政外交诸多重大问题;(3)梳理中日两国乃至近世东亚历史之演进,同时关注国际形势之风云变幻。具体到栏目上,除第一号系属草创,栏目格局略显纷杂外,自第二号起,归由法政大学主办,栏目经过调整、简化而趋于稳定,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栏目:
(一)主张。在创刊号中,此栏名为“社说”,类似今天刊物的开篇社论,或主题论文。大多涉及中国清朝内政外交方面重要问题,如《日清两国协办事业之第一步》(第一号)、《论清国立宪》(第二号)、《论清国利权回收》(第三号)、《论清国匪徒》(第五号)、《论支那移民》(第七号),等等。从作者署名和行文风格来看——大致从第三号起,每期此栏文章皆出自主笔久保天随之手。
(二)说林。此栏主要收集专业性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法律、政治、经济、历史乃至自然、社会等诸多方面。作者除法政大学所属教员,乃至法政速成科的教员(如梅谦次郎、美浓部达吉、小河滋次郎、河津暹、三上参次、山内正瞭、阿部秀助、乾政彦、中村进午)外,其他学界著名人士(如菊池大麓、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秋山雅之介、大江卓等)亦所在多有。具体文章来源,有的来自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讲演记录,如创刊号上刊载的三上参次《日支两国交际之回顾》、菊池大麓《理学及其应用》,与二人应邀在法政速成科毕业典礼上的讲演辞题目相同;而第二号刊载的梅谦次郎《条约改正与法典编纂》,则基本是其漫游中国归来的讲演报告。有的文章则来源于法政大学在读学生的作业,如何元瀚的两篇《因共有物分割所生之效果如何》及《禁地上权及永小作权让渡特约之效力如何》。有的文章则来自作者主动投稿,如大江卓的《东亚平和策》。其他有些文章虽然暂时来源或途径不明,但与日本法政大学和法政速成科之间或多或少应该存在关联。
(三)时论。在创刊号中该栏名为“时事反响”,主要转译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际媒体的时事报道,或相关评论文章。其内容基本以关涉东亚三国(中、日、韩)的新闻报道居多。经过初步统计,其所来源的日本著名媒体有:《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报》、《民声新闻》、《大和新闻》、《大阪时事新报》、《国民新闻》、《东洋经济新报》、《报知新闻》、《日本》、《新公论》、《报知新闻》、《日本及日本人》、《东西南北》。此外,部分新闻时事报道则翻译自一些欧洲新闻媒体,如《柏林泰母士》、《伦敦泰母司》(the times,泰晤士报)、《伦敦的黎米路》(daily mirror,伦敦每日镜报)等。新闻主题基本以国际时事为主,绝大部分牵涉到清朝的内政外交,对于今人了解当时国际舆论,很有裨益。
(四)杂俎。在创刊号中,该栏收录文章基本为东洋社成员自撰报道,涉猎相当广泛,如介绍张之洞和严修的家庭教育(《张总督之家庭》和《清国教育家严修及令息》)、中日凯发登录入口的版权问题(《日清间凯发登录入口的版权问题》)等。及至第二号,栏目发生改革:一方面,将“杂俎”一栏改为专门收录该社成员以及法政速成科学员之诗文作品,如选录主笔久保天随的《秋碧楼诗剩》与《秋碧楼文屑》;法政速成科第五班毕业生王时润的《闻鸡轩乐府》,也曾收录其中。另一方面,增辟一新栏目,名为“杂报”,将原属“杂俎”类文字,尽皆归入此栏。而在该栏目下,选译文章题目更趋多元,或记录当时清国留日学生的课外活动(如第二号《清国留学生作日本歌》)、或记述当时日本学界教育概况(如第二号《早稻田大学与支那留学生》),或谈论中国内政外交新闻(如第二号《清国留学生教育问题》、第三号《清国兴隆策》),其中不乏近代著名人物之逸闻轶事(如第六号《论岑春煊》、第八号《林公使对清谈》),诸如此类,颇能反映该东洋社成员对于当时社会时事之见解。
另在每期《东洋》杂志卷首,往往载有数幅人物或风景相片,卷末则有时附有若干独立作品,如《汉译改正刑法》、久保天随的《朝鲜现代史》,与前面的各栏内容一样,皆具相当史料价值。然在笔者看来,该杂志主要栏目(如“说林”)所刊文章,往往具有较高学术水准,或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因而更值得关注。谨将各期“说林”栏目下文章信息汇集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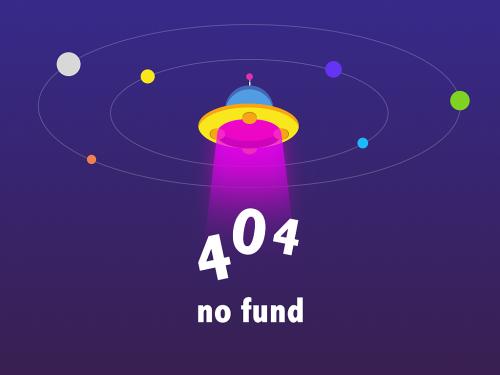

我们将各期连续刊布的文章合并统计,可以发现:《东洋》杂志“说林”栏目下全部文章共有32篇,内容上绝大多数为“政法”类专业文章。若将上述表格内容与当时法政大学速成科的课程设置、主讲教员名单逐一进行比对,更可发现,上述32篇文章的作者共24人,其中半数以上(13人)来自法政大学(包括教员和学生),甚至很多人担任过法政速成科的教员,只有少数是来自法政大学以外的作者。不仅如此,来自法政大学的13位作者共刊发20篇文章,占全部“说林”栏目文章的62.5%(20/32)。由此可知,当时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教员和学生(何元瀚)是“说林”栏目作者的绝对主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社说”或“主张”栏目下的文章(作者主要是久保天随)大多开宗明义,观点鲜明,每篇都值得仔细玩味。因为涉及《东洋》杂志思想特点的探讨,容下再作申论,此不赘言;(2)第三号“杂俎”栏目下刊有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文中译作“托尔斯多伊”)给当时清朝外交官张庆桐的通信翻译稿件(久保天随翻译)。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应属该信最早的汉文译本之一。不仅如此,在随后第四号“主张”栏目下,久保天随又针对上述通信,专门写就一篇名为《读托翁与清人某书》的评论文章。这封信的翻译件和久保天随的评论文章,对于解读托尔斯泰关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十分有益。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包括“时论”、“杂报”等栏目在内,该杂志的其他内容也都是难得的史料素材,需要研究者进一步阅读发现。
叁、《东洋》杂志的时代特征
现代媒体在发布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时,往往宣称:其所发布的媒体内容,并不代表该媒体观点。然而,作为历史媒体的研究者,却未必接受这套精致的说辞,往往会固执认为,媒体发布的任何内容,以及这种发布行为本身,即代表了该媒体的选择倾向。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将作为一种发布平台或渠道的媒体及相关从业者的思想倾向,和媒体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思想特征有意无意地加以混同。
以《东洋》杂志为例,作为一份内容多样、涉及多门专业知识的综合性刊物,其时代特征至少有三个可供探讨的思想层次:
一、《东洋》杂志组织发行者的思想特征;
二、《东洋》杂志所收录文章作者个别或共有的思想特征;
三、《东洋》杂志所代表的彼时日本知识精英的整体思想特征及其线索。本文主要着眼于第三层次,具体而言,就是试图通过《东洋》杂志刊载文章的整体解读,探析《东洋》杂志作者群体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于日本自身和彼时世界的认知观感,尤其对于清末中国内政外交的主要观点。
首先,我们不妨检视下作为杂志名称的“东洋”这一概念。直到今天,“东洋”在日本仍是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既有以之命名的著名学术期刊(如《东洋学报》、《东洋史学》),也有以之命名的社会组织或研究机构(如东洋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更有以之命名的著名图书馆——东洋文库。在中文中,“东洋”一般特指包括日本在内的南岛国家,或泛指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蒙古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或特指日本,此时基本和“东瀛”一词较为接近。在日语中,“东洋”(toyo)一词则一般泛指东方世界,或与英语中的“远东”(far-east)同一概念。
1906年《东洋》杂志创办之际,主事者心目中的“东洋”则别有一番含义。该杂志《发刊辞》开篇言道:“五洲广矣,种族众矣,而疆域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夥,莫若我亚细亚洲。而亚细亚建国之最久最著者,又实为支那、日本、朝鲜、安南。盖此四国,虽邦域之广狭,民俗之习惯,各有不同,而要其境界邻接,同文同种,伊古以来,玉帛通好,唇齿相依,独立于东洋,雄视于宇内,盖数千百载犹一日也。”显然,《东洋》杂志的创办者乃是立足亚洲(亚细亚洲),并将“建国最久最著”的中国(支那)、日本、朝鲜、越南(安南)等四个国家视为“东洋”的核心骨干。然在安南(越南)已经沦为法国殖民地的情况下,所谓“吾人国于东洋者,宜有协心戮力,研钻学术,启发知能,内敦其交,外御其侮,举同文同种、辅车唇齿之实,恢复往昔国运之隆,文物之盛,冠绝宇内”,究其实质,无外乎从日本立场出发,将利益或关注重点放在中国和朝鲜。
紧随其后,大隈重信、梅谦次郎等人在给《东洋》杂志的祝辞中,虽然也都极力称道该杂志企图维护“东洋和平之局”、“恢复往昔国运”的宏伟志向,但所谈论对象,尽皆以“支那”(中国)为言。我们同时不应忘记,该杂志特别采用了汉文形式出版印刷,并以清国留学生为重要发行对象。所以,基本可以肯定:这份《东洋》杂志的核心着眼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相较而言,1907年醇亲王应邀给《东洋》杂志题词——“志兴东亚”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最高当局对于该杂志或杂志的主事者,及其背后所依托的日本法政大学——乃至日本举国上下——一种美好的期许,希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能够把东亚振兴起来,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但不容否认的是,从“东亚”和“东洋”的不同表述来看,双方的概念理解从一开始便存在相当差距。
《东洋》杂志的主持者之所以对于“东洋”抱有如此“野心”,乃是基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至少包括:一、通过明治维新,系统改革内政外交,不仅使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得到增强,更从西方列强手中挽回了一度失去的国家利权;二、通过甲午战争,臣服朝鲜,战胜清朝,攫取大量战争赔款和殖民地,成功检验了日本作为新晋现代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三、经过日俄战争,不仅遏制了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势力扩张,更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新主宰,开启了日本迈向世界强国之林的新阶段。不言而喻,《东洋》杂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以今日视角观之,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所取得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外交等物质方面,更在于引入了一套崭新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并逐渐学会站在当时世界的知识前沿进行思考。正如时任法政大学校长的梅谦次郎在给《东洋》的祝辞中所言:“我邦自维新以后,锐意移入欧美文明之结果,驯至今日,粗得与彼比肩矣。”另从《东洋》杂志“说林”一栏来看,所收录论文大多具有学术性。类如美浓部达吉《近世宪法上之权力分立主义》(第一号)、小河滋次郎《犯罪者与妇人之关系》(第二号)、秋山雅之介《论战时病伤者之待遇》(第三号)、井上哲次郎《行为与目的之关系》(第四号)、佐藤丑次郎《论所基于自由主义之政治组织》(第五号)、中村进午《各中立国二十四时间之法》(第五号)、泽柳政太郎《教育与国家》(第六号)、河津暹《经济学上所见之家族制度》(第七号)、山内正聊《论政治之意义》(第八号)、古贺廉造《别卡理亚经历及其学说》(第九号)、乾政彦《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第十号)等,在于当日,内容皆属上乘;在于今天,亦有相当参考价值。
与上述社科或法政专业的教授学者们相比,从事“理学”(即理工科学)研究的菊池大麓亦未遑多让。他在杂志第一号《理学及其应用》一文中特别谈及“理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前景,言道:“今后斯学进步之所极,……在此二十世纪必当有异常发达之日。其所谓应用之影响者,勿论吾人生活上,于精神界,亦无不被大影响者。”“盖立国之道,在精神的与物质的之二方面,……理学之研究,实为国家进步上有大关系者”,故“自一国之品位上而言,当以学术之研究为国家急务也”。显然,菊池大麓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清楚认识到“学术研究”是“国家急务”,关系到国家进步或“一国之品位”。
犹有进者,久保天随在《论新学精神》一文中,鉴于当时清国留学生大举东渡,追求新学,特别指出:“然非人人自新,以一心灵动为主,则不过猕猴之智,模仿自喜者,安能得治世济时哉?凡讲新学者,必当领得自由灵活之心为之根柢,固不问其为何学也。”此中涉及知识学习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自由思想,即“自由灵活之心”。按照久保氏的理解,如果没有自由思想,缺乏“自由灵活之心”,则所学不过“猕猴之智”,通过模仿学习一点皮毛,便沾沾自喜,不济时用。相反,不论学习任何学问知识,尽皆需要以自由思想、“自由灵活之心”为根本。无独有偶,泽柳政太郎对清末进行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清朝政府发强迫教育之令,从小学制度到地方制度,固然可以花费大量国帑,顷刻成之,但制度贵在实行,只建立一些制度的空架子,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即便按照学部颁发章程,中学堂、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可以很快建立起来,但显然无法匹配新学应有之崭新精神。“苟精神而缺,则远聘师于海外,亦复何益,其形似矣,而其实非矣。”换言之,缺乏自由精神的教育体制除了大肆浪费民脂民膏,继续贯彻统治者愚民政策,根本不配称作“新学体制”,亦不可能造就崭新之国民。
正因为日本当时的知识界精英对于学术研究、自由思想和新学精神达成普遍共识,不仅为国家内政外交进步提供了崭新的知识驱动力,更成为国家文明进步的某种标志物,故而梅谦次郎情不自禁、相当自豪地讲“驯至今日,粗得与彼比肩矣”。对于当时日本内政外交之不断进步(或曰扩张),梅谦次郎因为其深厚学养,在行文中的表现尚属谦逊或带有几分保守;然而,有些日本人则表现得相当激进。尤其在日俄战争的胜利刺激下,日本社会上越来越弥漫着一股张狂之气。例如《东洋》杂志第九号,转载当时日本媒体《新公论》上面一篇名为《列国之气运》的报道,其中言:“日本民族……能制清、俄两国而获韩国,尽力于满洲经营,布哇、比律滨必不永为美国之有也。”“由是观之,将来能称覇于世界者,不过日、英、德、美四国。……国家间之事,唯力耳,力能作理,未有胜力之理也。”可以说,当时某些日本人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已经十分昭著了。
毫无疑问,十九至二十世纪日本某些方面的进步,是通过侵略或牺牲他国利益而获得的。《东洋》杂志《发刊辞》中所列举的“东洋四国”(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1906-1907年之际,越南早被法国占领,朝鲜也已通过甲午之战,被日本收入囊中,唯一在形式上保持国家独立的,只有老大帝国——中国。因此,中国自然成为日本战略上重点“经营”之区,俎上之肉。但基于两国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中日两国官府和民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尤其在甲午、庚子两役之后,大批清国留学生东渡扶桑,追求新知,企图仿效日本,挽救国家于危亡,恢复大国昔日荣耀。面对渡海而来的莘莘学子,以及这些学子背后、正在大兴改革的老大帝国,《东洋》杂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态度很是耐人寻味。
我们不妨重新回顾一下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写给《东洋》杂志的祝辞。在这篇祝辞例里,作为“日本民法学之父”的梅谦次郎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势力之强弱往往依赖人口多寡、国民贫富等物质因素,但在这些因素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国家强弱则取决于国民智识程度之高低。智识程度低者,则国家势力弱;反之,智识程度高者,则国家势力强。如果智识程度较高,则可能弥补其他因素的欠缺;如果智识程度低,则其他因素再高,也不免沦为弱国。不言而喻,在梅谦次郎眼中,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智识程度较低的一个典型。因此,教授清国留学生以政法专业知识,刊布《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和《东洋》杂志,其根本目的在于启发清国人民心智,提高其智识程度,使其国势由弱转强。梅谦次郎的这种想法,与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的某篇报道不谋而合,但似乎后者更进一层。该报道云,“自通商以来,列国对清国之方针,不适其宜也。何以言之?曰:列强之所求,在利权之占得,而不在文明之宣布,其所主在凌辱抑遏,而不在指导启发。”其中对于“列国”(主要是西方列强),明显带有批评,认为列强过于着眼于眼前利益争夺,竟不顾启发清国政府人民心智。因而,在该文作者看来,日本很有必要举全国之力,当启发之任,而“清国亦遣万余学生,留学我国都”,可谓适逢其会。
梅谦次郎等人之所以提出“启发”清国智识程度的口号,其逻辑前提在于他们认定中华帝国已经落伍于时代,落后于西方列强,甚至远远不及新兴的日本。与此相应,我们在《东洋》杂志中经常可以见到日本知识精英对于老大帝国守旧落后的批评性文字。即如上引《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便直言不讳:“清国开港以来,垂一世纪,与欧美人相接,不为弗久。……而清人之固陋思想,与守旧观念,今尚如昔日,比之半世纪前,无进境之可见者。”杂志第二号引用当时《读卖新闻》的报道,也说“大体而观,清国依然为守旧国,若欲使清国进于文明之域,则不可不尽力新思想之输入”。在当时众多日本学者看来,中国的落后守旧,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造成的必然结果。即如身为法政大学速成科教员的三上参次,在其《日支两国交际之回顾》一文中批评道:“支那自古自称中华,又中国,其环支那而立国者,称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以劣等民族视之,故日本与支那相交际,支那动以日本为附庸,而自处尊大傲慢,故我日本或敬而远之,或不以诚心待之。……故若仍存尊大自国,而蔑视日本为东夷之意见,则永久不能杜绝纷争也。不独对日本为然,将来对于诸外国,最不可不深自省也。”世界形势已然发生变化,中国如果依旧抱残守缺、妄自尊大,势必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当时日本学界之所以积极向清国留学生教授新学知识,试图启发清国人民和政府的智识程度,在《东洋》杂志中经常可以见到的两层理由是:报恩和自卫。用梅谦次郎的话说,“我邦汲汲然增进支那之知识者,盖一以报古昔所学于支那而进我文明之恩谊,一为我邦自卫之故”。“报恩”作为第一层理由,即便严厉批评清国一贯以来妄自尊大的三上参次也并不否认,他说“今日日本人而为清国人施教育者,则谓以先祖所尝受之恩,今日为之报复,亦无不可也”。梅谦次郎甚至坦言,之所以他对清国进行毫无顾忌的坦率批评,根本在于彼等先祖从清朝人的先祖输入文明,“而身被其恩,特尽言之,聊以为报恩之一方也已”。
如果说“报恩”尚能体现中日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那么作为第二层理由的“自卫”则显得较为直白,甚至有些赤裸裸。在大隈重信看来,“清国之盛衰,于东洋平和之局有最大之关系,故清国而一乱,则其害忽及邻国,实日本之祸也。不啻日本之祸延,迫害东洋之平和,搅乱世界之安宁,其祸乱之所及,何所底止。”故而,只有中国改善革新,“支那之文明始开,而东洋之平和于是乎定。此不啻东洋之幸,亦世界之幸也”。其实,除了表面上关注“清国之兴衰”外,当时所谓“自卫”的着眼点更在于防卫北方的俄国。三上参次在上引文章中说道,“试展舆地图观之,则日本与支那其北方有巨大一物而覆压之,日本与支那实有唇齿辅车之关系。故欲保东洋全体之和平,不可不同心协力,敦交谊,而当他之强敌。” 东洋社的“社友蠖堂”更是认为,日俄战争作为日本发动的“旷古之大战役”,其动机其实在于“自国防卫,为东洋和平,且为世界通商贸易,抑制俄国之横暴”。由此可见,俄国显然被日方排除在“东洋”概念之外,乃至在日俄战争后,仍被日方视作潜在敌人。因此,“启发”中国智识程度,倡导“东洋和平”,某种程度上无非是想笼络一位国交战略上的新盟友。
自事实层面观之,日方所倡导的启发智识、报恩自卫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无法掩盖其侵略掠夺的行为本质。一方面,假借提携中国之名,在中国东北大肆攫取利益。例如,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获得南满铁路及其沿线行政管辖权,此一行为在《东洋》杂志的主题评论文章中,被看作是一种正义之举,并将之提升到“日本精神”的高度。其言曰:“日俄交战之后,……以长春以南铁路归于日本利权者。要之,日本只代俄国地位耳。”“此铁路虽为俄国所让付,敷设于清国领土者,而日本固以维持东洋和平为本旨,故与俄国交干戈,实出不得已,丧生灵十余万,糜国财十数亿,渐达其目的。今组织此铁路公司,亦与清国官民相提携而经之营之,开发满洲富源,普及文化,增进两国福利,即是为日本精神也。”俨然将中国东北视作予取予夺的战利品,丝毫不顾及中国主权。无独有偶,政治学者江木翼在《略说胶州湾制度并论日本关东州》一文中,更是将日本新近占领的中国东北领土(“满洲”)——彼僭称为“日本关东州”,与德国所租借的胶州湾相提并论,公然视为囊中之物。另一方面,日方在报恩和自卫的双重理由下,公开鼓吹“保全清国领土”,所谓“以保全清土为第一义,锐意防止其瓦解者,不独因有唇齿辅车之关系。清国之灭亡,其危险亦可延及于日本故也”。该杂志转载《东京日日新闻》上面一篇报道,更俨然以“铁肩担道义”自诩:“(清国)在过渡之时代,其矛盾之思想,与撞著之政策,参差错综,而失误之极,将有转沦沟壑之虞。日本已致力于清土之保全,譬犹描巨龙之画工。自今以后,诱掖辅导,不可辞其点睛之任也。”
尽管当时日方对于清国态度复杂多端,具有不同层次的动机和利益追求,姑且不论其所持国家立场或强权逻辑,整体上,日本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对于清末进行的改革措施基本还是“乐观其成”的。即如大隈重信在给《东洋》杂志的祝辞中言,“千载一时,机不可失,愿清国臣民,同心协力,以举革新之实,实吾人之所以翘企不措也”,并且相信“清国政治之改革,必当如日本之核查各国之制度文物而采用之,而其将来于文明诸国之立宪政体,企望之,实行之,亦必当如日本也”。然而,鉴于彼国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以及日本当时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东洋》杂志的作者们对于中国求取新学、仿行新政之举,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虽然这些建议和意见背后难掩其试图进一步笼络中国、侵略中国的深层动机,但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镜鉴。
首先,在对待新学知识的态度和方法上,日方特别强调中国应该“广求知识于世界,以开国进取为国是”,放弃排外思想和一贯妄自尊大的虚骄姿态。在清国留学生大举东渡求学之际,日本方面对于这些留学生真实的学习动机亦有所理解。即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度废除后,大加提拔新学人才,“非有新学知识者,不能登龙门”。于是,“从来遵守科举旧制,准备登场者,皆转趋向新学,是所以老少杂然来学。”但是,这些赴东留学人员往往集中于“特殊学堂”(速成或专科),而平时交际又仅限于同国之人,因而很少与日本本国学生交游切磋,以致留学生越来越多,但并没有收到理想效果。
在日方看来,中国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也存在不少问题。《东洋》杂志第二号转载《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指出,当时清国留学生动辄以万数,“皆以改造祖国为志,固可为邻邦庆贺”,但令人忧虑的是,留学生所学多法律政治,选择工艺农商方面的学习者很少,“故其所论,有徒驰空理,疏远实学之弊”,采其难而舍其易,与学习屠龙之术无异,“实阻害祖国之改进前途”,而且与日方“奖励实学”的宗旨大相悖谬。究其实质,中国人在学习新知的过程中存在一种“速成心态”,避难就易,只图简单模仿,知其然而已,对于“知其所以然”却没多大兴趣。这一点与日本学习新知的做法,可能存在天壤之别。自觉发言毫无顾忌的法政速成科教员三上参次,谈到日本往昔学习中国的经验,“日本人之先祖所学于支那之事物,决不徒囫囵咽下,必咀嚼之,必玩味之,使优柔厌饫,悉化为日本之事物而后已,征诸政治、学问、风俗等百般社会事物而可知也。……此所以我日本人之进步,胜于支那人也”,因而他希望“今而后,支那之输入文明,亦须浑化改造之,以令适合于支那之实际,是为最要”。此中所言日本学习消化外国文化的方法和能力,可能直到今天仍经常被我们忽视,以致沉迷于“同文同种”的宏大叙事当中无法自拔。
另一方面,《东洋》杂志创刊之际,正值清朝大规模仿行立宪,进行政治法律改革,并企图藉此收回丧失已久的治外法权。该杂志第一号即转载一篇《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文章,意欲“告诫”清国国民,不要轻易挑衅外人,谨慎从事,否则“不啻利权不可回复,国力日削,外侮益甚”。主笔久保天随也不惮发出警告,“如轻躁极端之革命主义,不过倾危其国尔”。梅谦次郎基于日本法律改革三十余年之经验,也认为清朝的法典编纂和条约改正(即利权回收)不可操之过急,应该循序渐进:首先以养成法官为急务,其次司法、行政相分隔,法官独立,基础方开始牢固;再次,应该养成清廉之风。如果能够做到上述三项,“则条约改正,亦未为难事也。”
《东洋》杂志第二号上佚名发表的主题论文(“主张”),对于清朝预备立宪也持积极立场,认为“晚近旧梦渐醒,骎骎乎日新,进取之风气,将磅礴全国,苟善导之,扶植之,则可优具立宪国人民之资格也”。与此同时,该文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
“其一,清廷欲斟酌折衷欧洲各国及日本之制度文物,而厘革诸政,实施宪政,其意甚美。但欲仿效日本之所为,则宜讨究日本文明所由来,及其国体民俗所渊源,取舍折衷,适其机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若观察只限于皮相,遗其神髓,徒见外观之美而模仿之,依样画葫芦,则江南之橘必为江北之枳,不仅延误百年大计,更会招世人嗤笑。其二,宪政之实施,必须待宪法已经完成,准备齐整,而后可行。时间周期,至少应在十数年后,察其时机以施行宪政,决不可失之躁急。如果在人民智识未开、文明未进的时候,能力不足,却强力推行,就好比不能站立,却急于行走,没有不摔跟头的。立宪政治好比双刃剑,如果授受不得机宜,则授者受者,两被损伤。“上施其仁而不得为仁,下受其恩而不知为恩”,必然导致国家混乱。其三,清国版图庞大,各省割据独立,有尾大不掉之势。上情不通,下情不达,各地州殊其俗,县异其政,皆由于交通不便之故。所以,敷设铁路,通电线,开航运,以令全国气脉流通无滞,诚为当务之急。此外,地方自治和现代科学教育制度,也不可或缺,皆须提前预备。总之,一个国家宪法政治的建立实施,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精神和物质条件,方能成立。”
当然,除了相当多数知识精英对于清国立宪改革持积极态度外,也有人对此抱绝然相反的评价。即如杂志第九号翻译《东京日日新闻》上一篇报道,对晚清中国的政治前途不仅十分悲观,甚至认为清朝仿行立宪不过是“沐猴而冠”。其言曰:“若夫至太后百岁后,则为满汉之轧轹及南北之争斗,二三十年之间,恐无宁日。然如各省各独立树立共和国,勿论无之,其满汉分离亦必不能也。偶施行立宪制,所谓沐猴之冠,到底不可得好结果也。”与之相类,杂志第六号援引另外一份《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更是预言:“误清国前途者,非改革派与守旧派,实在两者之轧轹,与极端利权回收论者”。虽然这些评价和预言必符合实情,但清末改革过程中改革派和守旧派彼此倾轧造成的国力内耗,以及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某些颟顸的主张或冲动,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
最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面对二十世纪初期日本亟欲“启发中国”,所进行的“报恩”和“自卫”之举,当时中国留日学生作何感想?清朝政府和民间舆论又有何种反应?《东洋》杂志收录若干相关史料,可供我们管窥当时中国方面的思想反应。
即如《东洋》杂志第一号转载当时《读卖新闻》上的一则报道,首先援引某外国新闻记者的一则通信,进而谈到该外国记者曾经采访中国某留日学生,询问“日本人对支那人之交情奈何”。该留日学生回答说,日本人当时对中国人的态度大致可分三种:第一种为政治家,以及其他受过高等教育者。此类之人,皆认为中日两国休戚相关,属于“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故对中国之感情深厚,待遇也最为亲密。第二种日本国人,表面亲切,但内里将中国人视作劣等国民而鄙视之。第三种日本人最占多数,认为中国人是不能战斗之国民,因而大加轻侮。该留学生认为,之所以受到如此对待,与此前中国的屡次战败很有关系,“我支那人,欲受日本人之尊敬……则其可期乎?”相反,日本人欲求中国人之亲近和尊敬,也并不容易。日俄战争后,日本著名政治人物大江卓曾到中国游历,与中国缙绅交接会谈,也明显感到中国社会对于日本普遍抱有疑虑和恐惧。
另外,1907年7月左右,中国某媒体上一则报道引起《东京日日新闻》和《东洋》杂志注意。该报道大致云:“清国独立,不敢赖他国力,开放门户与否,亦方自决,不许他国干与也。曩者所发表之日法协商,为两国力行侵略而成者,将成之《日俄协约》趣旨亦必然。于是,日、英、俄、法之势力范围决矣,然则清国瓜分之端,将自是启。忧国志士,须奋起也。”如此看来,中国有识之士对于日本参与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野心是很清楚的。至于日方,也清楚知道,中国媒体往往背景复杂,“有系当路大官经营者,或有赖他国政府之后援者”,所以特别重视,不仅进行翻译,更公然对上述观点加以批判,乃至冷嘲热讽。该报道中言:“若清国力能保全其主权,维持东洋平和,则不俟他国之容喙与干涉……然国力不足,保持主权尚难,况整治所错综之国际关系,以维持东洋平和乎?”
总之,日本以维持东洋和平、恢复国运、启发清国为号召,以维持清国领土完全、报恩自卫为藉口,大肆进行侵略中国之实,其心昭然若揭。这样一种侵略野心和野蛮行径,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持续着。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自清末以来中日之间百余年的恩怨情仇,多种情愫混合在一起。对于某些日本知识精英企图通过教育启迪中国人智识程度之举,也并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含有真实的“报恩”成分,但在现实具体的国家利益面前,频繁上演的则是一出出恣意的侵略和杀戮,以及无情的攻击与反抗。当我们今天翻阅这份尘封已久的《东洋》杂志,感觉历史的硝烟并未散尽,而解决未来所有问题的关键,可能还需要仰赖古老的中华智慧,极高明而道中庸,化干戈为玉帛。



